精品小说《开皇行者:我的隋朝奋斗史》,类属于历史古代类型的经典之作,书里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李椿,小说作者为山河知晓,小说无错无删减,放心冲就完事了。开皇行者:我的隋朝奋斗史小说最新章节第14章,已更新了230982字,目前连载。主要讲述了:大兴城的夏夜闷热难当。亥时刚过,天际滚过一阵闷雷,随即,暴雨倾盆而下,砸在瓦片上噼啪作响,仿佛要将整个大兴城彻底淹没。李椿处理完手头的公文,吹熄了书案的油灯,躺下来。就在他意识逐渐模糊,即将睡着时,院…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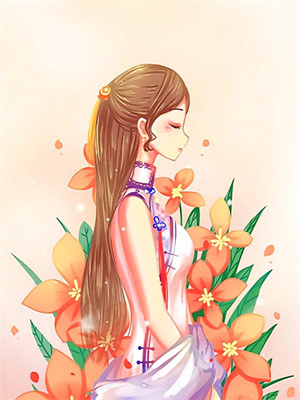
《开皇行者:我的隋朝奋斗史》精彩章节试读
大兴城的夏夜闷热难当。亥时刚过,天际滚过一阵闷雷,随即,暴雨倾盆而下,砸在瓦片上噼啪作响,仿佛要将整个大兴城彻底淹没。
李椿处理完手头的公文,吹熄了书案的油灯,躺下来。就在他意识逐渐模糊,即将睡着时,院门处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
李椿瞬间清醒,这么晚了,又下着大雨,会是谁?他伸手从枕头下摸出一把短刀。
“谁?”他提高声音问道,同时悄无声息地走到门后,身体紧绷。
门外没有回应,只有更急促捶门声。
李椿握紧了刀,再次问道:“门外何人?何事深夜敲门?”
这时,一个清晰的声音传来:“晋王府。”
晋王府?李椿心中一凛。拔开门闩,将门拉开一条缝,向外望去。只见门外站着一名身披油衣的男子,正是晋王杨广的随身侍从。在他身后,两名黑衣人腰佩横刀,骑着马,立在雨中。
“李文学,殿下召见,请你入府议事。”那侍从说道。
“殿下为何深夜召见?”李椿心中疑虑更深,试探着问道。
“卑职只是奉命行事,余者不知。请李文学速速上马,莫要让殿下久等。”侍从侧身让开,做了一个请的手势,态度强硬。
李椿知道多问无益,回头看了一眼内室方向,深吸一口气,转身返回屋内,抓起一件外袍披上,便踏入雨中,利落地翻身上了侍从牵来的马。马蹄踏在积水的青石板上,溅起水花,一行人很快便消失在雨夜中。
晋王府内,李椿被引至杨广的书房外,侍从示意他独自进去。杨广站在窗前,望着窗外暴雨肆虐的庭院。
“臣李椿,参见殿下。”李椿躬身行礼,衣角还在滴滴答答地淌着雨水。
杨广缓缓转身,“免礼。”他走到书案前,示意李椿近前,随后拿起一份奏报。
“李椿,”他语气平缓,“你可知,前周武帝灭齐时,北齐户籍在册人口逾两千万?而如今我大隋一统南北,历经父皇十年治理,最新统计的户口,却仍不及此数。”他放下奏报,目光扫过李椿,“北齐富庶甲于天下,然政令昏聩,终至亡国。其府库充盈,却尽入我大隋之手。可见,国库丰盈,未必是社稷稳固之基。”
李椿沉思片刻,谨慎答道:“殿下明鉴。北齐之亡,在于失道。府库之财,若不能惠及百姓,反成催命之符。我朝立国,轻徭薄赋,与民休息,乃是正道。然……若因政令宽仁,致使奸猾之徒隐匿田产人丁,逃避朝廷赋役,长此以往,恐伤国本。”
“隐匿人丁田产……”杨广微微颔首,踱到一幅巨大的舆图前,目光落在关陇一带,“此确为顽疾。高相推行大索貌阅,收效显著,括得新附人口百余万。然数年过去,此风似有再起之势。尤其是一些开国元从、地方著姓所在的州郡,上报的户口田亩数字,年年相差不多,与朝廷预估,总是有差距。”
他转过身,目光锐利地看向李椿:“譬如岐州,下辖六县,地处关陇要冲,土地肥沃,水利便利。然其上报户数,常年维持在四万余户,口二十万上下,增长极为缓慢。这与当地物产、商贸之繁荣,似乎并不相称。孤近查阅旧档,发现北周时岐州极盛时期,在册人丁远多于此。这数万差额的人丁,以及他们所耕种的田亩,究竟去了哪里?”
他走到书案前,手指轻轻点在那叠关于岐州的文书上,声音依旧平稳,却带着无形的压力:“前几,孤向父皇举荐,派你以钦察特使之名,前往岐州,专司核查户口、清丈田亩之事。此地情况复杂,牵涉颇多。你此去,首要之务是查明实情,将隐匿的人丁、田亩清查出来,充实国库。其次,也要看看地方吏治民情,究竟如何。孤予你临机专断之权,但切记,”他加重了语气,“分寸二字,重于千钧。过刚易折,过柔则靡。如何拿捏,看你本事。”
李椿知道,这是杨广在给他一个巨大的机会,同时也是将他推向风口浪尖。他无法拒绝,只能深深躬身:“臣,领命。定当竭尽全力,厘相,不负殿下所托。”
“三后动身。所需人手、一应文书凭证,明会有人与你交接。”杨广挥了挥手,重新转向窗外,结束了这次召见。
离开王府,雨势稍歇,李椿穿行在寂静无人的坊街。这趟差事,恐怕比他想象中还要凶险百倍。那“分寸”二字,说起来容易,做起来,无异于刀尖跳舞。
回到家中后的李椿身心俱疲,带着满脑子的思绪和一身湿冷,几乎是沾枕头就睡着了。
然而,刚睡着没多久,一阵敲门声又将他从沉睡中硬生生拽了出来。李椿烦躁地用被子蒙住头,不想理会。敲门声停歇了片刻,就在他意识再次模糊,即将沉入梦乡时,更急促的拍打声响起,伴随着喊声:“李文学!李文学可在?”
李椿猛地掀开被子,一股被惊扰了好梦的无名火直冲头顶,他低声嘟囔着:“你最好有事!”他胡乱套上鞋子,沉着脸,走到院中,刷地拉开门闩。
门外站着一个年轻人,见到李椿,先是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,随即又换上一副担忧的模样。“李文学!您可算出来了!”
李椿皱了皱眉,认出了这人。之前在街上遇到刘三时,这个人就站在刘三身后。“你是……刘三身边的人?”
“是是是,小的名叫刘安!李文学您真是好记性!”刘安如同在汹涌波涛中抓住了唯一一救命稻草,声音都在发颤,“李文学,求您发发慈悲,救救三爷吧!三爷他被官府抓起来了!”
李椿心头一跳,但面上依旧不动声色:“刘三?他一个市井商人,所犯何事?”
“他们……他们说三爷伪造户籍、私贩官营物资……这、这可是头的重罪啊!”刘安带着哭腔,“小的知道不该这么早来麻烦您,惊扰您清梦,可三爷往那些朋友,如今都躲得远远的,连门都不让进。小的实在走投无路了,三爷平最是仰慕您的人品才学,小的只能厚着脸皮来求您了!”说着,他竟噗通一声跪在地上,“李文学,求您看在往三爷对您还算恭敬的份上,救三爷一命吧!三爷待我恩重如山,我这条贱命不值钱,若能救出三爷,我刘安以后就是您的人了,当牛做马,绝无怨言!”他一边说,一边不住地磕头,额头沾满了泥水。
看着声泪俱下的刘安,李椿心中的火气消散了,取而代之的是一丝无奈和疑虑。刘三虽是个混迹市井的人物,有些上不得台面,但对他一直毕恭毕敬,也确实提供过一些有用的消息。更重要的是,在这个他即将前往岐州的关键节骨眼上,刘三突然出事,而且罪名直指“户籍”和“官营物资”,这仅仅是巧合吗?
“你先起来。”李椿叹了口气,声音缓和了些,“我可以随你去看看情况,但能否救他,如何救,需依律法而行,我无法给你任何保证。”
刘安闻言,如蒙大赦,又重重磕了两个头,这才颤巍巍地爬起来,连声道谢:“谢谢李文学!谢谢李文学!您肯去看看就好,去看看就好!”
李椿回屋快速换了身爽的常服,束好头发,便跟着刘安前往关押人犯的京兆府狱。到了京兆府狱大门外,刘安迫不及待地冲到守门的狱卒面前,陪着笑脸深深一揖:“公人安好。小的想探视一个人,名叫刘三,前刚送进来的。”
那狱卒上下打量着他:“刘三?那个伪造官凭、私贩禁物的奸商?”
“正是正是,”刘安腰弯得更低,“公人明察。小的就是在他铺子里帮忙的,想来给他送些吃食…”
“不行!”狱卒厉声打断,“他是重犯!没有长官手令,任何人不得探视!快走!再在这里纠缠,连你一并抓起来!”
刘安急得连连作揖:“公人,烦请通融,小的就看一眼,说句话便走…”
“说了不行就是不行!”狱卒不耐烦地挥手驱赶,“再啰嗦现在就锁了你!”
刘安焦急地想要争辩,与狱卒推搡起来,动静引来了一旁的人。那人原本靠在墙边打盹,被吵醒后骂骂咧咧地出来,目光不耐烦地扫过,但当落在李椿身上时,他愣了一下,随即脸上瞬间堆起谄媚的笑容,快步上前,拱手笑道:“哟,这不是李文学吗?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?”
李椿看了看此人,并无印象,微微蹙眉:“足下认得我?”
“小的吴朗,之前曾在晋王府外院当差,有幸见过李文学您几面。”吴朗态度恭敬,“现在京兆府狱混口饭吃。王府上下谁不知道,李文学您学识渊博,深得晋王殿下器重。”他瞥了一眼还在与刘安纠缠的狱卒,转而问道:“李文学今来此,是……?”
李椿指了指一脸焦急的刘安,平静说道:“我一位故旧被拘在此处,想来探问一下具体情况。”
那之前呵斥刘安的狱卒听到这番对话,赶紧凑过来,赔罪道:“小的有眼无珠!不知是李文学,冲撞了尊官,还望李文学恕罪!恕罪!”态度瞬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,与方才的凶神恶煞判若两人。“既是李文学,自无不可,请进,快请进!”
刘安见状,脸上不禁露出一丝扬眉吐气的得意笑容,挺直了腰板,跟在李椿身后。
在吴朗的引领下,李椿和刘安顺利进入了监牢。狭长而昏暗的甬道里,弥漫着一种令人作呕的味道,不时还传来囚犯的呻吟。在一间狭小肮脏的牢房里,他们见到了刘三。
见到李椿,刘三如同濒死之人看到了最后一稻草,猛地挣扎着扑到栅栏前,声音嘶哑带着哭腔:“李文学!李文学您可来了!救我!我是被冤枉的,是被人下了套啊!”
“别急,慢慢说,到底怎么回事?”李椿沉声问道,示意他冷静。
刘三急忙道:“前些子,有个生面孔找到我,说有一批货,主要是锦、绫,还有些农具,有官凭的,要运到陈仓县。开价极高,高得离谱。我本不想接这不明不白的生意,”旁边的刘安忍不住嘴证实道:“是啊,李文学,三爷当时还跟他说,运货该找正经镖行,我们不做这个。”刘三苦笑一声,脸上满是悔恨:“可那人说信不过镖行,就指名要我的人脉和路子,说三爷在道上信誉好。而且他给出的官凭,我看着印章、格式都像真的……一时鬼迷心窍,贪那笔厚利,就……就答应了。谁知货刚到陈仓县地界,还没进城,就被当地官府连人带车截住,人赃并获!他们当场就说那官凭是伪造的!我……我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啊!”他捶打着栅栏,涕泪横流。
“此事我已知晓。”李椿沉默片刻后说道“你暂且安心,我会设法查清原委。但能否救你,需依律而行,我无法给你保证。”
刘三感激涕零,隔着栅栏连连作揖:“多谢李文学!多谢李文学!”
离开京兆府狱后,李椿回到了家中,独自坐在书房里,开始复盘刘三的事。陈仓县?岐州辖地?李椿眼神骤然一凝。这事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浓浓的蹊跷。运货为何偏偏找上刘三?他一个市井人物,有什么能力往岐州运货?是刘三无意中得罪了不能得罪的人,被陷害?还是……
正苦思冥想间,院外传来赵二虎那熟悉而爽朗的笑声:“李兄弟!在家吗?快出来看看某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!”
话音未落,人已大步流星地直接推开虚掩的院门走了进来,手里高高拎着一个酒坛,脸上洋溢着热情的笑容:“瞧瞧!正宗的河东桑落酒!醇厚着呢!前几带兄弟们破了一伙盘踞多年的盗匪,尊官赏的!今说什么也要与你喝个痛快!”
李椿暂时压下心中的疑虑,起身迎了上去,脸上露出笑容:“赵兄今怎得有暇过来?”
“刚交了差事,尊官开恩,赏了半休沐!”赵二虎将酒坛“咚”地一声放在院中的石桌上,震得桌面微颤,他仔细打量了一下李椿,浓眉皱起,“兄弟,你这脸色可不太好啊?苍白得紧!可是昨晚没睡安稳?”他注意到李椿眉宇间化不开的凝重。
李椿请赵二虎坐下,没有隐瞒,将昨夜晋王雨夜召见以及即将前往岐州的事,简略地说了一遍。
赵二虎闻言,刚刚还笑容满面的脸立刻沉了下来。他拍开酒坛的泥封,给两人面前的碗里斟满酒,”岐州……”他压低了声音,身体前倾,”那地方,水可浑得很!某早年随军在那附近驻防过一阵子,那些地方上的世家大族……嘿,个个都是坐地虎,土皇帝!别说寻常官吏,就是刺史、别驾去了,办事也得先看他们几分脸色,小心翼翼供着。”
他端起碗喝了一大口,抹了抹嘴,继续道:”兄弟,你这差事,听着光鲜,实则是趟浑水,棘手的很啊!哥哥我听署里一些老吏私下议论,这些盘踞地方的世家大族,为了保住祖传的田产和荫庇的人口,什么阴狠毒辣的手段都使得出来,人不见血!而且他们在朝中的关系更是盘错节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”
两人你来我往,几碗桑落酒下肚,李椿听着,目光注意到赵二虎右肩处绑着绷带,隐隐渗出血迹。赵二虎注意到他的视线,咧嘴一笑,浑不在意地拍了拍伤处:”皮糙肉厚,前两追贼时挨了一下,不碍事,过几便好了。你此去,人生地不熟,千万要小心,万事留个心眼!”
李椿看着赵二虎脸上的担忧,心中不由一暖,在这冰冷的权力漩涡中,这份质朴的兄弟情谊显得尤为珍贵。他喝完酒的脸颊泛着红,忽然微微一笑,那笑容里带着一种让赵二虎看不懂的复杂意味。
赵二虎被他这突如其来的笑容搞得一愣,停下倒酒的动作,有些茫然地看着他:“李兄弟?”
李椿凑近赵二虎,赵二虎先是一惊,随后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,皱着眉闭上了眼睛。
李椿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话。
赵二虎听到后睁开了眼睛,随着李椿继续说,惊讶的瞪大眼睛,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,随即,他看了看李椿坚定的眼神,猛地一拍大腿,哈哈笑道:“成!既然兄弟你心里早有沟壑,成竹在,那某就放心了!”他端起酒碗,与李椿的碗重重一碰,仰头豪饮而尽。
赵二虎走后,李椿不知道是酒醉还是一夜未睡,倒在床上就睡着了。
次一大早,李椿再次踏入晋王府。杨广在书房亲自将盖有皇帝御玺的正式文书交到他手中,又拿出一块新的铜制腰牌,正面刻着:晋王府,背面则是:关陇察访 李椿,字样。“此行责任重大,拿着这块腰牌,或可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”杨广语气平淡,但眼神中带着期望。
李椿恭敬地双手接过,谢恩之后,退出了王府。站在王府门外的高阶上,他低头看着手中的敕文和王府腰牌,突然,他脑海中灵光一闪,一个大胆的计划瞬间成形,嘴角不由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。
他没有回家,而是径直再次来到了京兆府狱。或许是换了班,今守门的狱卒面生,见他衣着普通,又要探视重犯,立刻板起脸阻拦:“去去去!说了重犯不能探视!快走!”
此时,站在另一侧昨那名狱卒认出了李椿,脸色一变,急忙上前,抬手就给了那名狱卒后脑勺一巴掌,骂道:“瞎了你的狗眼!此乃晋王府上的李文学!还不快滚开!”随即转身,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,点头哈腰地对李椿道:“李文学恕罪,新来的不懂规矩,您请进,快请进!”
李椿脸上挂着笑容,点了点头,正要迈步进去,却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,停下脚步,转向那名狱卒,语气随意地问道:“哦,对了,我有公在身,你们的长官可在?”
“在的在的!小的这就带您过去找司法胡参军!”狱卒连忙在前面引路。
来到胡参军处理公务的屋外,狱卒识趣地先行离开了。李椿整了整衣冠,脸上挂着那抹人畜无害的笑容,迈步走进屋内,叫了一声:“胡参军。”
那胡参军正埋首于一堆卷宗之后,似乎正在为什么事情烦心,头也没抬。
过了一会才从鼻子里哼出一声,语气十分不耐烦:“什么人啊?找我什么事?”
李椿也不生气,依旧站在原地,语气平和地说道:“下官李椿,是晋王府的人,奉晋王殿下之命,前来……”
那胡参军一听到“晋王”二字,如同被针扎了一般,猛地抬起头,脸上那点不耐烦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,随即迅速化为热情的笑容,他站起身来,连连拱手:“快请坐!快请坐!”他亲自搬过一张胡凳,用袖子拂了拂并不存在的灰尘。
见李椿从容坐下后,胡参军才小心翼翼地在对面坐下,陪着笑脸继续问道:“不知尊官前来,所为何事?”
李椿也不绕圈子,直接问道:“胡参军,请问狱中可有一名叫刘三的犯人?”
胡参军闻言,脸上露出一丝思索的神情,随即打开手边的犯人名册,手指顺着名单往下滑,口中念道:“刘三……刘三……哦,找到了!前几由岐州那边押解过来的,罪名是伪造市籍,私贩官营物资,现关押在重犯监区。不知……尊官为何突然打听此人?”他抬起头,眼中带着疑问。
李椿面色不变,淡淡道:“奉晋王殿下命,需将此人带走。”
胡参军脸上笑容僵住了,为难地搓着手:”这个…尊官,即便是晋王殿下,没有敕书,下官也不敢私自释放重犯啊。这…这不合规矩…”
“那是自然。”李椿从容起身,从怀中取出那份御玺文书,”胡参军请看。”
胡参军一眼认出那明黄色的卷轴和上面的玺印,双手微微发颤地接过。就在他正要展开细看时,李椿突然掏出晋王府腰牌,”啪”地按在文书上。
“胡参军,”李椿声音陡然转冷,”不知参军可识得此物?”
胡参军盯着那”晋王府”三个字,额头渗出细密汗珠:”自然识得,自然识得…”
“那还不快去提人!”李椿猛地提高声调,脸上尽是怒容,”耽误了晋王殿下的大事,你担的起吗!”
胡参军被这突如其来的呵斥吓得一哆嗦,哪里还敢细看文书,连忙躬身道:”尊官息怒,下官这就去提人!”说着匆匆出门吩咐狱吏。
李椿趁他转身,迅速将敕书和腰牌收回怀中。胡参军回头时只见他负手而立,虽心中仍有疑虑,却也不敢多问,只连声道:”尊官稍候,刘三马上带到。”
不多时,两名狱吏拖着一个人进来。李椿看到眼前景象,手中茶碗险些脱手 ——只见刘三被打的血肉模糊,浑身是血,脸上肿得睁不开眼,正迷迷糊糊的看着李椿。
李椿本想去搀扶,突然又坐下,他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引起怀疑,只冷冷道:”安排一辆马车,将犯人送到晋王府。”
看着刘三被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,李椿心中有些动容。马车行至晋王府前街转角,李椿突然叫停:”就到这里,犯人这般模样,莫要惊了殿下。”
待马车远去,他这才搀扶着刘三,一步步挪回家中。
郎中为刘三诊治后,对李椿嘱咐:”皮肉伤虽重,幸未伤及筋骨。这药膏每换一次,汤药早晚各一剂。切记忌食辛辣,好生静养月余方能痊愈。”
刘安红着眼过来接过药,送走郎中后,突然扑通跪地。李椿连忙去扶,他却死活不肯起身,一个劲地磕头:”李郎君,从今往后我刘安这条命就是您的!”
李椿与柳芸娘对视一眼,皆是无奈。柳芸娘柔声道:”刘家兄弟快起来,让你三爷好生歇着才是正理。”
三后,晋王府外。三名文书随从和两名护卫已经整装待发。李椿正要上马,却见刘安气喘吁吁地跑来,”扑通”一声跪在马前:
“明公!小的这条贱命是您的,您到哪我就到哪!听闻您要去岐州,刘安愿追随左右,当牛做马!”
李椿尴尬地环视四周:”快起来,成何体统!”
“您不答应,小的就跪死在这里!”
“此去三百余里,你无马如何跟得上?”
“小的能跟上!绝不敢耽误行程!”
李椿见他目光坚定,只得无奈应允。一行人出了城门,马蹄扬起阵阵尘土。行至马嵬坡时,李椿回头望去,却见刘安竟还紧随队尾。
“真乃奇人…”李椿不禁感叹。
到了马嵬驿,驿夫热情迎出:”尊官里面请。”另外几名驿夫过来牵走了马匹,李椿盯着大门外,迟迟不见刘安身影,正疑惑间,却见他快步跑进驿门,气息微乱:”李郎君!”
李椿无奈的笑了笑:”进屋歇脚吧。”随行众人见刘安竟徒步跟到这里,拍了拍刘安肩膀,皆是连连称奇。
众人围坐在驿馆大堂用饭时,刘安先是仔细为李椿布菜,又忙着给众人斟酒。一名文书忍不住问道:”刘安,你这脚力是怎么练的?”
刘安腼腆地笑了笑:”小的自幼家贫,常要翻山越岭采药换钱。后来在商队做脚夫,从大兴到洛阳,三便能走个来回。这些年走惯了,倒也不觉得辛苦。”
护卫张诚拍着他的肩膀:”从大兴城一路跟到马嵬驿,你这脚力,怕是比驿马都不差了!”
刘安腼腆地低头:”小的没别的本事,就是脚力好些。”
李椿默默听着,目光在刘安身上停留片刻。这个看似普通的市井之徒,身上似乎藏着不少秘密。
入夜后,刘安伺候李椿洗漱更衣,连洗脚水都试好了温度。待李椿躺下,他又仔细检查门窗,将李椿的衣物叠得整整齐齐,这才在离开。
李椿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发呆,若有所思,窗外月色朦胧,树影摇曳,很快便睡了过去。
深夜驿站内传来一阵动,先是几声惊呼,接着是兵器碰撞发出的声响。
随行的一名护卫在屋外敲响李椿房门:”李文学,有匪盗劫驿站,李文学快起身!”
李椿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惊慌失措,本能的去拿枕头下的短刀,没有摸到,想起来自己此时身处驿站,兵刃收到行囊中了。他匆忙披上外衣,刚推开门,就被护卫护着往走廊深处退去。
从走廊向驿站门外望去,只见几名驿戍已倒在血泊中。李椿正要转向楼梯,却正好被门外走进的劫匪看到。这些劫匪全都用黑布包着头,蒙着面,只露出一双双凶狠的眼睛。劫匪拿刀指向李椿大喊一声:”别动!”
此时三名劫匪冲上楼梯,护卫张诚大喝一声迎上前去。他手中横刀挥动,直取当先那名劫匪的咽喉。那劫匪急忙举刀格挡,两刀相撞迸出火星。另外两名劫匪趁机左右夹攻,张诚临危不乱,一个侧身避开左侧劈来的刀锋,反手一刀刺向右侧劫匪的口。
此时旁边屋内也走出几名劫匪,看到这个情形,果断去控制住了一旁的李椿。
张诚见状想要回援,却被三名劫匪死死缠住。他怒吼一声,刀势陡然变得凌厉,一个斜劈将一名劫匪的手臂斩伤,但另外两名劫匪的刀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上。
护卫终究寡不敌众,被劫匪制服,两人都被绑住带到院子,李椿转头看到另外一名护卫和随行都已经被绑住也在院子里,可他四处观望却没有看到刘安,地上又躺着好几具尸体,看不清刘安有没有在那里,心中不禁一沉。
此时一名劫匪过来,用刀柄砸向李椿:”看什么看!”李椿脸上顿时鲜血直流,另一名身材消瘦的人走了过来,站在李椿面前,示意先住手,随后看向李椿。
李椿注意到他们的刀柄都有一个不显眼的鹰隼标记,很眼熟但他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。
随后那人看到李椿的衣服里似乎藏着什么东西,伸手拿出来,是敕书,李椿顿时慌张,挣扎着想站起来,被旁边的人按住:”老实点!”
那人打开敕书,看着里面写的内容,然后若有所思的合上。
就在这时,远处传来马蹄声响,一大队人马正往这里赶来,那人赶忙把敕书扔在李椿面前,直勾勾的盯着李椿,眼神锐利,令人不寒而栗。
门外的一名劫匪喊道:“是县尉,快走!”然后一行人上马逃离了。
随后县尉带着戍卒骑马去追击匪盗,其余几名戍卒进了驿站,李椿看着来人,惊讶的喊出:”刘安?”
刘安下了马,飞快的跑到李椿面前给他松绑:”李郎君可安好?小的夜里在马厩,看到一伙人蒙面持刀进来,了驿戍,想进来告知李郎君,可那伙人堵在门外,小的进不来,便乘其不备,前去县衙报案,县丞听闻在马嵬驿,也没听我说完,就派人去调县尉前来。”刘安说话时气息十分急促。
李椿站起身询问众人有没有受伤,随行人员都说没事,一旁几名戊卒相视一眼,径直走进屋内,随后李椿让刘安去给他们松绑,自己则跟着走进屋内查看,见到那几名戍卒推开每个房间的房门,像在寻找什么,随后几人停在了一间屋外,查看一番后,便下楼和李椿擦肩而过,匆匆离开了。
一旁李椿的随从走了过来,嘴里说着:”如此便走了?”
李椿看着那间屋子和戍卒的背影,若有所思,心中疑云更重。
此时驿长听到屋外没了动静,这才带着其他人从屋内走出,吩咐人收拾残局。
李椿见状,指着楼上那间屋子上前询问:”这屋内住着何人。”
驿长顺着李椿手指的方向看去,顿时脸色大变,跑上楼查看,李椿也跟了上去。只见驿长进到屋内后,就四肢瘫软的坐到地上,很快脸上就从震惊转变为绝望,哭着说:”我命休矣!”
李椿向屋内看去,只见几名护卫倒在屋内,桌上行囊里东西洒落一地,似乎是被人翻检过,一名穿着绸缎长衫的男子倒在血泊中,死状惨烈,浑身被砍到血肉模糊,头颅也被割下,滚落到一侧,似乎跟凶手有血海深仇。
李椿见到眼前这幅惨状,胃里一阵翻腾,跑出屋外。扶着墙壁呕不止。
此时其余人也走了上来,其中一名驿夫走过来,满脸愁容:”这该如何是好啊,我等性命不保了。”
一旁的刘安看着他这个模样,不解的说道:”死的可是你爷娘?”
“……”驿夫没有理会他。
“人的可是你?”
“……”
“你这驿夫甚是奇怪,既然人不是你的,你怕甚?像死了爷娘一般”,刘安继续说道。
李椿见状示意刘安住口,接着上前一步,正色道:”我乃晋王府文学侍从李椿,奉晋王命,前来岐州公。你且说清楚,这死者究竟是何人,为何让你们如此惊慌?”
驿夫上下打量了一番李椿:“是…韦潼”见众人脸上没有一点反应,他又继续说道”尊官不知韦家?”停顿了片刻后继续说道,“罢了,如今我命也不久矣,尊官随我来。”
随后一行人被带到大堂坐下,驿夫从屋内拿出一壶酒,倒在碗中,自顾自的大口喝了起来,众人见状皆不明所以,几碗酒下肚后,驿夫面如死灰,压低声音:”尊官莫怪小老儿失态,您可知如今大兴皇宫里,管着陛下衣冠的尚衣奉御、守着中书省机要的中书舍人,那都是韦家的故吏!这京兆韦的,是扎在宫墙里头的!”
他手指着西边:”从这马嵬驿往西三十里,所有浇地的渠水都要先经韦家田。今年大旱,上游闸门一落,下游五个村子饿死大半——就为让他家新辟的鹿苑多几汪活水。”
又指指驿马:”这些官马平吃的草,都要从他家牧场高价采买。连岐州兵府的战马配给,都要看他韦氏点头。”
突然扯开衣襟露出鞭痕:”上月有驿卒不慎惊了韦家女眷车驾,第二便在井里浮着了。县衙来查案,却说…失足。”
“这韦潼如今死在此处,韦公一怒,这驿站上上下下,连同家小,怕是连岐山的乱葬岗都进不去!”
“在岐州,韦家的意思就是王法。你看到的是一片太平,这太平底下,埋得可都是不服之人的骨头啊!”
听完这些话的李椿回过神,注意到此时众人都看着他,心中疑惑。而刘安似乎也听说过这些事,开口问道:”李郎君从未听过?”李椿不解的看着他。
此时天色渐明,驿夫们还在收拾残局。
“即刻启程。”李椿对众人吩咐道,”此事关系重大,必须尽快赶到雍县。”
刘安默默整理好行装,目光在那间厢房停留片刻。
众人收拾好行囊,出发继续前往雍县。晨雾尚未散尽,谁也不知道迎接他们的是什么。
小说《开皇行者:我的隋朝奋斗史》试读结束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