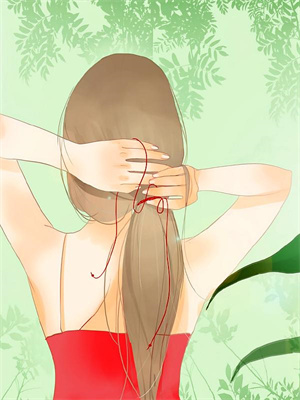简介
历史脑洞小说《寒门青云路:我在大景考状元》是最近很多书迷都在追读的,小说以主人公林牧之间的感情纠葛为主线。没有笔墨的洲作者大大更新很给力,目前连载,《寒门青云路:我在大景考状元》小说144756字,喜欢看历史脑洞小说的宝宝们快来。
寒门青云路:我在大景考状元小说章节免费试读
正月十六,年节的气氛尚未完全散去,但汴京城的日常节奏已然恢复。文华斋开门营业,活字印刷的订单开始增多,张掌柜忙得脚不沾地。林牧的生活也重回备考的轨道,晨诵暮读,午后蒙学,规律得近乎刻板。徐焕赠的那块钢胚镇纸,稳稳地压在他的书案一角,黝黑沉静,偶尔在灯下反射出冷冽的光,提醒着他那个迥异于科举文章的世界。
随着县试日期的临近,一种无形的压力开始弥漫在汴京城众多备考的学子之间。茶楼酒肆里,谈论时政的声音少了,切磋经义、揣摩考题的议论多了起来。各种版本的“今岁县试主考官偏好分析”、“近年命题趋势”、“必读范文汇编”开始在书坊间悄然流传,价格不菲。
林牧没有去追逐这些“秘籍”,周文渊所赠的《策论精要》已是最高明的指南。他按照册子上的提示,重点温习了《孟子》和《春秋》,因为近三年县试策论多从此二经出题。同时,他也开始有意识地收集市井民情,不是刻意打听,而是在蒙学课后与来接孩子的家长闲谈,或是在帮张掌柜整理新书时留意书中的时事评论。他知道,一篇出色的策论,除了经典的支撑,还需有对现实的洞察。
正月二十,赵铁柱再次来到文华斋,取走了钱三公子订制的五十部《幼学琼林》注本。他没有多停留,只是在付清尾款时,看似随意地对张掌柜提了一句:“北边不太平,市面上流言多,掌柜的和林先生都当心些,莫要听信传言,安心做自己的事。” 这话看似寻常提醒,但出自兵部的人之口,分量便不同了。
张掌柜心领神会,晚间对林牧道:“看来北疆之事比想象的更麻烦。朝廷必有动作,只是如何动作,还在博弈。这段时间,咱们少议国事,尤其莫要与人争论边策战和。”
林牧点头应下,心中却想,这或许正是自己策论可以着力的方向——不直接评判战和,而是探讨如何固本培元、增强国力以应万变。他将这个思路记下,准备作为策论练习的一个方向。
正月廿五,距离县试只剩二十天。这天下午,林牧正在书房揣摩一篇以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“天时不如地利,地利不如人和”破题的策论,试图引申到边关防守中民心、军心、物资保障等“人和”要素,前堂伙计忽然来请,说有位老先生指名要见他。
来到前堂,林牧见到一位须发皆白、精神矍铄的老者,穿着半旧的儒衫,手里拄着一根竹杖,正站在书架前浏览。听到脚步声,老者转过身,目光温和而深邃地落在林牧身上。
“学生林牧,见过老先生。不知老先生召见,有何指教?” 林牧拱手行礼。
老者微微一笑,声音苍劲:“老朽姓韩,单名一个‘庸’字。前几日听坊间老友提及,文华斋有位少年蒙师,教导有方,更难得的是自身勤勉向学,志在科举。老朽闲来无事,便来瞧瞧。”
韩庸?林牧觉得这名字有些耳熟,随即想起,张掌柜曾提过,汴京有位致仕的韩老翰林,学问渊博,性情淡泊,莫非便是此人?
“学生些许微末之技,不敢当老先生谬赞。” 林牧态度愈发恭敬。
韩庸摆摆手,走到那间临时的蒙学教室门口,看了看里面的小黑板和沙盘,点头道:“法无定法,贵在得宜。你能因地制宜,以沙盘减幼童畏难之心,以口诀增其记忆之趣,这便是‘得宜’。蒙学乃文教之始,始正,则后路不偏。” 他转过身,目光落在林牧脸上,“听闻你备考县试,可有疑难?”
这几乎是在主动提出指点了!林牧心中惊喜,但想起周文渊和郑怀安的告诫,又强自按捺,谨慎答道:“学生正在研读《春秋》,于微言大义,常感力有不逮。”
“《春秋》笔削,一字褒贬。” 韩庸缓缓道,“然初学者往往陷于字句考据,或流于空泛大义。须知圣人作《春秋》,是为乱臣贼子惧,更是为后世立纲常、明得失。读《春秋》,当知时、知势、知人。时不同,势不同,人之所为与所得褒贬亦不同。譬如‘郑伯克段于鄢’,若只论兄弟阋墙,便失了深意。当思其时郑国内忧外患之局,思庄公之隐忍与无奈,思‘克’之一字所蕴含的痛惜与决绝。”
这番见解,与周文渊册子中“重实务、明得失”的观点隐隐相合,但更侧重于历史情境的理解。林牧听得入神,躬身道:“学生受教。”
韩庸似乎谈兴渐浓,又就《孟子》中几处容易误解的章句略作点拨,言语精辟,每每切中要害。末了,他似无意般问道:“你既读《春秋》,当知‘居安思危’之义。如今北疆不靖,朝野议论纷纷。若以此为题,你当如何破局?”
问题再次指向时政。林牧心中警铃微作,但见韩庸神色坦然,目光清澈,不似刺探,更像是师长考校学生见识。他略一思索,答道:“学生浅见,‘居安思危’不仅在思边患之危,更在思国力之基是否稳固。边患如疥癣,可御可抚;国力若衰,则如膏肓之疾。故策当以固本为先:劝农桑实仓廪,整军备修武库,明赏罚聚人心。本固则枝荣,纵有外患,亦有应对之资。若舍本逐末,空议战和,恐无裨益。”
他没有直接回答“如何应对北疆”,而是拔高到“固本”的层面,这既安全,也显得更有格局。
韩庸听罢,抚须沉吟片刻,眼中赞赏之色更浓:“不局于一隅,能见大体,很好。少年人有此见识,难得。” 他从袖中取出一本薄薄的、纸页泛黄的手抄册子,递给林牧,“这是老朽早年读《春秋》的一些札记,或许于你有助。县试在即,望你戒骄戒躁,沉着应考。”
林牧双手接过,只觉得这册子虽薄,却重若千钧。“学生何德何能,受老先生如此厚赠……”
“学问之道,薪火相传罢了。” 韩庸笑了笑,不再多言,拄着竹杖缓步离去,背影消失在熙攘的街市中。
张掌柜这才从柜台后走出来,看着林牧手中的册子,叹道:“这位韩老翰林,致仕多年,深居简出,等闲人求他一字而不可得。今日竟主动来见你,还赠以心得……林牧,你的机缘,真是令人惊叹。”
林牧抚摸着册子粗糙的封皮,心中并无多少得意,反而感到压力又重了一分。周文渊、郑怀安、徐焕、韩庸……这些人物交织成的网,将他托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,也让他更清晰地看到了平台之下的激流暗礁。这些馈赠与期许,都是需要他用实力和成绩去偿还的“债务”。
正月廿八,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悄然在汴京流传开来:奉命前往北疆调查军屯被袭案的钦差队伍,在边境附近遭遇小股马贼袭击,虽未造成重大伤亡,但仪仗受损,颇为狼狈。更有传言说,袭击者并非普通马贼,而是伪装了的赤狄游骑。朝廷震怒,主战之声一时高涨。
气氛明显紧张起来。街上的巡城兵丁多了,各城门的盘查也严格了些。文华斋里,偶尔有客人低声谈论此事,语气忧虑。张掌柜叮嘱所有伙计,不得参与议论。
林牧则注意到,来书坊购买或翻阅兵书、舆图的人,似乎又多了一些。但他谨记张掌柜和周文渊的告诫,只做不知,将所有心神都投入到最后的冲刺中。他将徐焕的钢胚、韩庸的札记、周文渊的精要,并排放在书案上,仿佛三座沉默的山峰,提醒着他前行的方向与重量。
二月初一,距离县试仅剩三天。按照惯例,县学会在考前最后几日开放“考棚”供学子熟悉环境。林牧带着考牌和文房,前往位于汴京县学旁的考院。
考院占地颇广,气象森严。高墙环绕,门口有兵丁把守。前来熟悉考场的学子排成长队,依次验看考牌后方可入内。气氛肃穆,无人喧哗。
进入院内,是一排排低矮的号舍,密密麻麻,如同蜂巢。每个号舍仅容一人,内有木板一块充作桌案,矮凳一张,墙角有炭盆(但考试时未必有点燃的炭),此外别无他物。号舍之间以砖墙隔断,前方敞开,但有栅栏,便于考官巡视。
林牧找到自己的“甲辰七十三号”舍,进去试坐了片刻。空间狭小,光线昏暗,若是阴雨天气,恐怕更难熬。他试着研墨、铺纸,模拟考试时的动作,感受桌椅的高低是否合宜。又抬头观察前方巡视通道的视野,心中默默规划考试时如何摆放物品,如何应对内急等琐事。
周围陆续有其他学子进来,大多面色凝重,低声与同伴交流。林牧听到有人抱怨号舍太窄,有人担心如厕问题,也有人在小声猜测今年主考官的偏好。
“听说了吗?今年主考官可能是新任的汴京知县杨大人,这位杨大人可是出了名的严格,尤恶浮华文风。”
“未必,我听说是府学的一位教授……”
“管他是谁,咱们只管把文章写得花团锦簇……”
“花团锦簇?你没听说杨大人务实?我看得多引经据典,方显功底……”
林牧默默听着,并不参与。他知道主考官是谁固然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文章本身是否立得住。周文渊的册子里已分析过几位可能主考的风格,他心中自有定见。
熟悉完考场出来,天色已近黄昏。刚走出考院大门不远,斜刺里忽然走过来一人,挡在林牧面前。来人二十多岁,衣着华贵,面容带着几分骄矜,身后跟着两个小厮。
“你就是林牧?”来人上下打量着他,语气不善。
林牧停步,拱手:“正是在下。不知阁下是?”
“我姓李,李修文。”来人扬了扬下巴,“清溪县李修远,是我堂弟。”
李修远?林牧想起来了,是当初在清溪县学嘲讽他拿不出二两银子作保费的那个富家子。看来这位是他在汴京的亲戚。
“原来是李兄,失敬。”林牧态度平和。
李修文哼了一声:“听说你也在备考今岁县试?还找了国子监的郑博士作保?倒是有些门路。” 他话锋一转,带着讥讽,“不过,科举凭的是真才实学,不是攀附了谁就能高中的。我堂弟修远,家学渊源,苦读多年,今岁志在必得。你一个……呵呵,还是莫要抱太大希望,免得到时落差太大,承受不起。”
这是赤裸裸的挑衅和压力了。林牧面色不变,淡淡道:“李兄说得是,科举凭的是真才实学。学生才疏学浅,只知尽力而为,至于结果,自有考官定夺,非你我可妄议。若无他事,学生告退。”
他不欲纠缠,侧身欲走。李修文却跨出一步,再次挡住,压低声音,语气带着威胁:“小子,别以为有郑怀安保你就万事大吉。汴京城的水深得很,你最好识相点,离某些人远些,安心考你的试。若是挡了不该挡的路,或是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……哼,就算有保人,也未必护得住你!”
这话里的暗示已经相当明显。林牧心中一沉,看来李家不仅知道郑怀安作保,很可能还隐约察觉到他与周文渊或徐焕的接触,甚至……可能与漕运案或钱三公子那边有些关联?
他抬起头,直视李修文,眼神平静无波:“学生听不懂李兄在说什么。学生只知道闭门读书,准备应考。至于其他,学生一概不知,也一概不想知道。告辞。” 说罢,他不再理会李修文难看的脸色,径直绕过他,大步离去。
走出很远,仍能感到背后那道阴冷的目光。林牧深吸了一口初春傍晚微凉的空气,将方才的遭遇压在心底。威胁与压力,也是这条路上必须面对的考验。他握了握袖中的考牌,木质的棱角硌着掌心,带来一丝真实的痛感。
二月初二,龙抬头。林牧没有出门,只在文华斋后院安静地收拾考篮:笔墨纸砚务必齐备且顺手,镇纸(他选了另一块普通的,徐焕所赠太过扎眼),水壶,少许耐饥的干粮(张掌柜特意准备的肉脯和面饼),一件厚实的旧披风以防考场寒凉。每一样东西,他都反复检查,摆放有序。
张掌柜来看他,见他神色平静,动作不疾不徐,赞许道:“沉稳就好。记住,进了考场,莫管他人快慢,按你自己的节奏来。经义题务求稳妥,策论题则要抓住要害,言之有物。你这些时日的准备,足够了。”
傍晚,陈大福竟也来了,提着一包热腾腾的茯苓糕。“明日就要进场了,吃这个,顶饿,寓意也好。”老乞丐看着林牧,浑浊的眼里满是殷切,“小子,别紧张。你比那些绣花枕头强多了!好好考,考完福伯请你喝酒!”
林牧谢过,送走陈大福。夜色渐浓,他没有再读书,而是早早洗漱躺下,闭上眼睛,在脑中最后一次梳理可能遇到的题型、破题的角度、可用的典故,以及……那些可能隐藏在考题之外的、来自现实世界的干扰与考验。
窗外,汴京城渐渐安静下来。但在这静谧之下,有多少学子和他一样辗转难眠?又有多少双眼睛,在暗中注视着这场即将开始的、或许能改变许多人命运的考试?
二月初三,寅时正刻(凌晨4点),林牧准时醒来。窗外还是一片漆黑。他起身,用冷水洗了脸,仔细穿好那身浆洗得挺括的靛蓝直裰,将头发一丝不苟地束起。吃过张掌柜准备的清淡早饭,检查了一遍考篮,然后对着铜镜,整了整衣冠。
镜中的少年,眼神清亮,面容尚显稚嫩,但眉宇间已有了超越年龄的沉静。他知道,踏出这个门,他便要独自面对这个时代给予他的第一次正式考验。
张掌柜、李师傅、杨文远,甚至几个相熟的伙计,都等在前堂,默默为他送行。没有多说什么,只是用眼神传递着鼓励。
林牧对众人深深一揖,然后提起考篮,转身,推开了文华斋的大门。
门外,天色微熹,寒风料峭。通往考院的街道上,已有不少手提考篮、形色匆匆的身影。林牧汇入这沉默的人流,向着那座森严的考院,一步一步,坚定地走去。
县试,开始了。